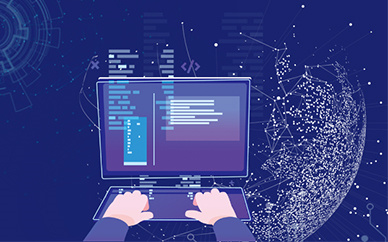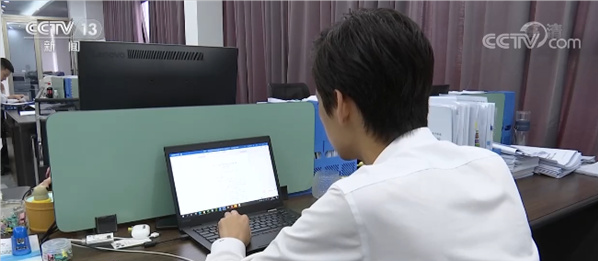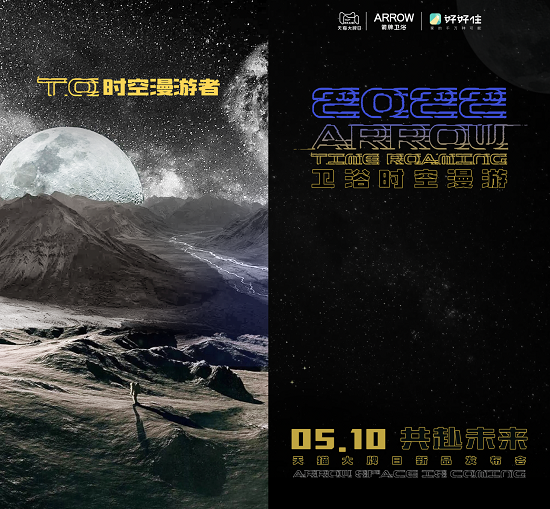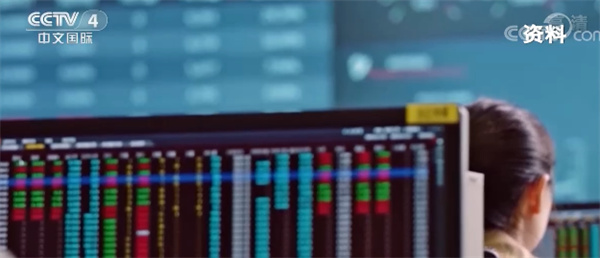来源:靳毅投资思考
出于对资本外流风险的担忧,年初以来央行谨慎宽松。部分观点认为,随着人民币贬值进入中期,汇率风险部分缓释,外资会重新流入,对央行政策宽松及债市均形成利好。但我们认为,拥有套保工具的外资,理论上可以规避汇率风险,因此购买境内债券更多考虑中美名义利差。所以随着下阶段中美利差延续倒挂,资本外流压力将持续存在,央行很难大幅宽松。
而在经历了一轮牛市之后,当前利率债配置价值一般。在央行难以大幅宽松的前提下,利率债收益率下行空间,远小于可比的2018年人民币贬值时期。
与此同时,有部分投资者担忧人民币贬值带来输入型通胀风险。但我们发现,人民币贬值的背后,外需与出口通常同步下降。无论是出口商品转内销增加国内商品供给,还是外需疲软导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均对国内通胀有更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输入型通胀,不太可能成为下阶段央行的主要考量与债市交易主线。
1、汇率的涟漪
4月下半月,人民币开启快速贬值阶段后,债市投资者对于汇率走势的关注明显升温。但是汇率与“宽货币”、“宽信用”等因素不同,对于债市的传导机制,似乎并不明朗。
因此,我们试图探讨当前人民币贬值,对于债市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在债市会泛起怎样的涟漪?为了使探讨过程更清晰,我们选取了当前市场上三个有关汇率的观点,进行针对性的分析,最后总结结论。它们分别是:
(1)人民币贬值周期中,债市多牛市;
(2)外资卖债行为,仅在汇率贬值初期出现;
(3)人民币大幅贬值,会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
1.1
人民币贬值多“债牛”?
目前市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贬值期间,经济下行压力通常加大。为对冲经济下行,央行往往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为利率提供下行动力。
此种观点的证据是:回顾2015年“汇改”以来汇率与利率的联动,就会发现汇率下行期间,债市多出现牛市。例如:2015年6月至2016年7月、2018年4月至2018年11月、2019年4月至2019年8月。
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当前的债市我们就会发现,本轮人民币贬值周期中,债市环境与历史不同,不同点有2个:
不同点一:美联储的货币紧缩力度,达到了2015年“汇改”以来之最。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以及美国通胀持续超预期的影响,年初以来美联储紧缩表态与市场预期不断升温。
1月FOMC会议前夕,海外投资者预计2023年6月美联储加息顶部在2.5%以下。而到了5月初,市场预计2023年6月美联储加息顶部已经提升至3.5%-3.75%。
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大幅升温,带来了美债利率的快速上行,并导致目前中美国债利差已经倒挂——这是“汇改”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中美利差倒挂带来的资本外流压力,显然已经引起了央行及相关决策者的警惕。例如1月降息后,全球通胀环境升温、美联储加速紧缩,导致央行并未在2月份连续降息。而3月底,上海疫情爆发以来,尽管疫情严重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稳定,但央行仅降准0.25个百分点。
当前央行的操作也符合历史的惯例,即“中国央行从未在美联储加息周期中,进行过降息”(具体内容请参考1月18日报告《还会有下一次降息么?》)。目前,央行“稳增长”主要依靠结构性货币工具,例如近期推出科技创新再贷款、普惠养老再贷款等。
不同点二:经过2021年一轮债牛之后,当前长债利率下行空间较往年更小。同样是美联储加息期间人民币贬值,2018年4月份,10年期国债利率高于MLF操作利率30BP以上,在这个点位利率债具有较高的配置价值。因此尽管2018年全年央行并未降息,仅实施了降准等数量型操作,债市利率也能下行。而当前,10年期国债利率却略低于MLF利率,配置价值一般。
所以综合来看,美联储超预期的紧缩操作,带来相对应的资本外流压力,显然对中国央行降息形成掣肘。而若央行不下调政策利率,当前市场利率的下行空间,显然比2018年小得多。
1.2
资本外流,仅在汇率贬值初期出现?
虽然资本外流压力,会对央行的宽松操作形成掣肘。但也有观点认为,出于对汇率贬值风险的防范,资本外流行为仅在汇率贬值初期发生。在人民币贬值中后期,随着汇率风险得到缓释,外资反而会重新流入。因此当前这一阶段,资本外流与外资卖债行为即将过去,对央行的掣肘即将消失,并对债市形成利好。
这一观点的证据是:2018年年中、2019年年中及2020年2季度,从人民币贬值中期开始,境外机构重新开始大额增持境内债券。
但是“防范汇率贬值风险”这一理由,并不能解释为何2018年四季度至2019年一季度,人民币汇率停止贬值乃至转向升值期间,外资依然净减持了境内债券。一个更有说服力的逻辑是,拥有套保工具的外资,理论上可以规避汇率风险,因此购买境内债券更多只考虑中美利差。而2018年四季度至2019年一季度,中美利差持续位于低位,因此即使人民币彼时已经恢复升值,外资流入依然较少、乃至为负。
所以我们判断,随着中美利差倒挂幅度加大、倒挂时间延长,下一阶段外资卖债压力仍将存在。
而在具体券种上,根据中债登与上清所托管数据,外资持债主要集中于国债、政金债这两个品种。同时,考虑到政金债流动性要比国债更好,短时间内外资集中卖债,对国债利率的冲击高于政金债。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何2月底以来国开隐含税率逐步下行。
1.3
汇率贬值,带来输入型通胀风险?
有观点认为,人民币大幅贬值后,以美元计价的进口商品价格抬升,带来输入型通胀压力,对债市形成明显利空。
但此种观点忽视了,人民币贬值的背后,外需与出口通常同步下降。无论是出口商品转内销增加国内商品供给,还是外需疲软导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均对国内通胀有更明显的抑制作用。从历史上来看,2015年“汇改”后至2016年上半年,以及2018年年中至2019年三季度,人民币贬值期间,核心通胀均出现下行态势。
因此输入型通胀,不太可能成为下阶段央行的主要考量与债市交易主线。
2、总结
基于对上述三种观点的分析,我们总结认为:出于对资本外流风险的担忧,年初以来央行谨慎宽松。而下阶段中美利差延续倒挂,资本外流压力不减,央行很难大幅降息。
而在央行难以降息的前提下,尽管目前面临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但债市利率下行空间,远小于可比的2018年人民币贬值时期。
与此同时,虽然输入型通胀不构成债市利空因素,但疫情后宽信用起步、以及持续性的外资卖债行为,均带来长债利率上行风险,需要投资者予以关注。
风险提示俄乌冲突升级,美联储超预期紧缩,中国央行货币政策超预期,新冠疫情传播超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