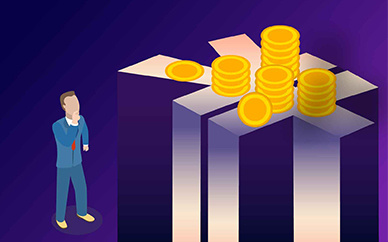导语:
在智慧医疗领域,脑科学和脑认知的突破给神经系统疾病的诊疗带来了新格局。近年来,各国政府投入巨大,先后发起脑科学计划,尝试破解更多大脑的秘密。在“第十届华兴资本医疗与生命科技领袖峰会—智慧医疗圆桌论坛”中,几位嘉宾分享了对脑机接口修复脑损伤的看法、高质量商业化落地的路径和经验,同时畅想了未来国内脑科学发展的前景。希望本篇论坛内容为您带来对于脑科学的新认识。更多峰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论坛嘉宾:
宁益华|景昱医疗创始人兼董事长
彭 雷|脑虎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宋冬雷|冬雷脑科创始人兼院长
赵瑞麟|应脉医疗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1. 脑机接口修复大脑损伤
主持人:感谢各位嘉宾莅临论坛跟大家交流脑科学前沿的话题。Neuralink的创始人Elon Reeve Musk(埃隆·马斯克)在很多场合说原则上脑机接口技术可以修复任何大脑损伤,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嘉宾的观点。
赵瑞麟:马斯克有优势,他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对于脑科学,本身人类知之甚少,比起别的行业,比如心血管,已经是大家很熟悉的领域,而脑科学有很多根本的问题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有些问题我们是知道的,比如神经系统真正的死亡是不可能恢复的,神经细胞和心脏细胞都是这样的,笼统说脑损伤都可以用脑机接口解决这个话说的我认为还是有夸大的。
脑机接口有它的好处,前面几个论坛从基因角度、微观角度、蛋白角度分析各种各样关于脑的疾病,真正的脑科学我认为应该从宏观角度解决这些疾病,从不同的角度,各个方面配合。再往前讲,现在神经调控这类技术其实都是使用综合性的手段来解决脑科学的一些问题。
彭雷:我特别同意赵总的回答,马斯克本身就是一个超级网红,他的话题自带流量,但是看马斯克所做的所有业务里面,包括Space X、特斯拉、Starlink以及SolarCity,其实本质上强调的是工程能力,解决的是成本问题。马斯克业务里面难度最大的是Neuralink,因为Neuralink是唯一的一个有大量的科学问题要回答,同时有大量的工程挑战要解决,还要控制成本的项目。他在这个领域里面带来的正面影响是通过他巨大的影响力让这个市场被更多人关注。但是无论获得什么样的关注、有再多的资本注入,都不会改变这个行业的本质。我们对脑科学基础的研究,包括工程、工艺、半导体、芯片、算法、植入体各方面的能力提升,要到一定时间点才有可能突破。
这也是为什么脑科学成为“人类四个大科学计划”里面的第四个大科学计划,前面三个分别是四十年代的原子弹“曼哈顿计划”,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90年代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脑科学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包括从去年9月份开始国家启动的计划,未来10年会有500亿的投入,不是简单通过一个脑机接口解决所有问题的,里面有大量的技术工作要做。
这样回头看,马斯克在这个行业里面产生的影响力是好事,但是要脚踏实地把产品、工程、工艺各方面的能力堆叠到一个程度,才有可能实现突破式的跃迁。这是我们对这个领域应有的态度。
宁益华:景昱十多年来在脑刺激和信号调控方面做了很多研究,包括临床和生物学方面的研究。关于脑机接口,如果仅仅有干预和感应的功能,应用会比较狭窄,脑机接口应该作为与感应和干预同步的接口性的技术,通过感应和干预达到两个层面的效果。
第一个层面是大脑塑形的变化,整个脑细胞会在思维、运动各个方面产生一套塑形。脑深部刺激或者脑的刺激干预可以改变大脑的塑形,从而治疗很多疾病。
第二可以帮助病人进行代偿。很多特定功能缺失的病人可以通过脑刺激等方式来代替原本缺失的功能,这也是脑接口能够解决的问题,未来进一步发展可以形成功能替代,这是未来的技术。
我认为应该分成两个层面看这个问题,谢谢。
2. 脑机接口的临床落地
主持人:非常感谢宁总的回答。刚才讲了第一个题材,Neuralink相关的,有跟专业医生相关的问题我们想展开问一下冬雷脑科创始人宋冬雷院长,您认为脑机接口的哪些应用会率先进入临床?
宋冬雷:非常高兴能跟各位探讨这个问题,各位看脑子的机会不多,但是我们作为神经外科医生天天看脑子,到现在我打开1万个脑子是有的。但是这个技术我也很好奇,外科医生也很好奇,大脑里面这些信号传递是怎样实现的。
刚才讲的两个内容,一个是从脑到机,一个是从机到脑,前者是把人的意识转化成信号,在外面接收,比如不能动弹的,通过脑机接口让手动起来,甚至眼睛失明的能看见。后者是通过外部的信号调控人的大脑。
这里面有一部分工作已经实现了,像景昱医疗有一些产品已经在临床上使用了。比如对于帕金森病的治疗,我们临床疗法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靠他们的产品,植入到大脑中找到靶点进行参数调整,控制这个疾病,改善症状,这个是临床上正在做的。对于昏迷的病人,我们用电刺激仪埋到颈椎能够刺并激促进病人的恢复。
这些技术已经在临床上有越来越多的应用了,但是更深层的一些问题要解决,目前还早。比如通常讲的脑机接口,通过脑部跟机器之间的信号传递,一方面调控脑,一方面指挥其他的系统工作,这方面我认为还是像刚才所说的,存在大量的技术问题需要研究,目前临床上没有看到实际的应用。
主持人:所以宋院长您觉得脑机接口距离临床还是很遥远的,很难预判。
宋冬雷:很难预判从哪个角度应用,但局部的调控或者单病种的调控,这个已经开始了,包括戒毒、精神病、抑郁症等等都可以通过这种微创的调控手术进行改善,这离临床已经不远了。但是更大范围的应用,比如埋芯片到大脑,把大学的课程埋到大脑里,大家不用上大学了,这种技术我觉得还是很遥远的。
主持人:下面能不能请宁总把刚才宋院长提到的戒毒、强迫症等等可以进入临床的脑科学领域的进展和大家分享一下。
宁益华:我们作为探索脑科学的一分子,这十几年来景昱先把帕金森产品做出来,我们跟专家一起合作,进行科学的探索。我们探索了很多神经生物学疾病的原理,根据脑深部刺激本身的机理,提出了新的治疗方案,也获得了专利,这些治疗方案在精神相关的疾病,包括毒瘾、强迫症等,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这个成果我们在脑科学领域算是First in Class,也是一路走过来的。
这里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思维逻辑,特别是在脑科学领域业务发展的逻辑。我们现在人类有很多新的技术,工程学的技术也走得很前沿了,包括马斯克讲的脑机接口的技术,从业务角度或者从公司角度来看,应该要完全聚焦在怎么治疗一个疾病上面,把工程技术拿来治病,而不是仅仅追求工程技术的某种非常高端或者高技术的实现,一步步来,任何的高端技术都是要适合于真正的应用、真正的治疗或者诊断。把别人诊断不出来的疾病诊断出来,把别人医治不了的疾病治好,这种应用就是高端应用,而不是一味追求高端技术。
这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经验分享给大家,要朝着这个方向走。
赵瑞麟:我特别同意宁总的观点,现在很多脑机接口技术在工程学上面临挑战,比如Neuralink所在的领域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基本的问题都没有回答。展开来讲,比如意识存不存在,人体大脑的CPU有没有记忆物质化,如果记忆物质化可以理解成编码方式,那记忆就可以存储,当然这个还非常遥远,跟哲学有关系。我们能不能了解这些物质,真正理解我们是否有意识的存在,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
主持人:彭总您认为脑机接口哪些应用可以率先进入临床?
彭雷:刚才讲得很清楚了,宽泛地看脑机接口已经存在20年了,从DBS、SCS到RNS等,本质上讲都是神经调控类的产品,针对明确的适应症,在脑机这个领域里做适应症为导向的应用研究,这已经是存续20年的事情了。
为什么现在火起来?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这些适应症,大脑很多适应症发病的原理到现在都没完全解释清楚,只知道这种治疗方式有效,电极放在某个位置帕金森病就没有了,但是原理是Neuralink没有回答的。
现在大家关注的脑机接口,如果从脑功能区来讲,从原始的内部爬行脑区到皮层层面上一些高级功能,从人的感知到认知,刚才赵总讲了在认知层面上我们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我们的记忆、灵性和更高级的能力要哲学来回答,但是基础的一些爬行脑区病症可以通过刺激来解决。
但是认知层面上,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感知方面,脑机接口可能出现进展,这也是为什么以马斯克为代表,引起了一些关注,因为现在已经有大量科学文章、论文证明了,比如皮层语言区的读取可以做到语言的合成、文字的描写,我们在血管里面放支架电极能够做到两三个自由度选择的判断,这些是过去三五年很重要的突破。
所以大家臆想我们有没有可能从刺激到皮层的读写,再到记忆、意识、情感等更高级的能力,这从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但可能每一个阶梯的跨越都要10年、15年,但是我们相信它需要一群人,无论是来自于医疗器械、神经科学背景的人,还是芯片、材料、算法、互联网、AI背景的人,整个产业链许多交叉学科、不同背景的人一起研究,才有可能找到这个答案。
但是我们生而为人,探索内心的奥秘是每一个人都会思考的问题,像康德说的,终其一生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就是头顶的星空跟心中的道德。我们会持续探索这个奥秘,但是需要一代一代人、一群一群人努力,这是我觉得从应用型的脑机接口到更宽泛的脑机接口,到终极的叫“缸中之脑”或者数字孪生、数字永生的概念,都可以畅想的。
中间应该有一条路,这条路需要一代人去探索,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去探索这条路。
3. 迈向高质量的商业化
主持人:现在做脑科学的企业很多,资本也在追逐这个方向,但是医疗领域还是需要有耐心的,如何在脑科学领域高质量地实现商业化?现金流什么时候能回来?
彭雷:很好的问题,马斯克花了3.6亿美金,七年的时间,到现在一例临床没做,零收入,他说的有不计代价的钱可以投入,他有全球第一网红的标签,他可以这样做,但是我觉得中国做脑科学不应该这样。
脑虎虽然我们成立只有10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非常认真考虑我们钱从哪来。我们业务第一阶段选择是科学市场,中国有大量脑科学基础工程需要研究,这个领域里面无论是电极、芯片、硬件、软件、算法基本上都是进口的,我们先帮助中国的神经科学家更好地研究大脑,背后又有脑计划,我们先卖给科学家做动物实验,这是我们选择的第一个市场。
第二才是医院,找临床的适应症,比如说高位截瘫等等,跟帕金森还不一样,我们会选择不同的适应症,但是我非常同意宁总说的,要选择清晰的应用做针对性的医疗器械。
第三个阶段是我们基于对于这个技术充分的了解,也了解了大脑的原理,各项工程能力也具备了,我们再去用在普通人身上,那就是消费电子的市场,可能真的需要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在座的各位可以立一个小目标,我们有生之年一定会在大脑中植入电极,只是三十年、二十年还是十年的事情,等到那个阶段我们收入模式又不太一样了。
这是脑虎从科研、医疗再到消费这样一个路径的选择,解决资源跟收入的问题,我们肯定不能像马斯克那样烧钱。
主持人:感谢彭总提到,商业化第一步是科研,第二步是医疗。我想问一下宋院长您觉得商业化在临床医疗这个市场怎么看,从资本角度认为这个钱什么时候能回来?
宋冬雷:彭总讲的已经很好了,第一步可能用在科研上,因为这个东西肯定从科研开始,从技术实验、动物实验开始的,这一步我们医生可以跟他们合作,要做动物实验,医生肯定要出点力,所以在科研上是第一步的,毕竟科研也是有投入,也可能有产出的。
第二步,在特定的适应症上,在一些技术已经做好的情况下,像宁总的这些产品已经可以商业化了,已经有一些在用了,无非是现在用得不多,不多就是需要更多的资料,还需要更多的医生关注,还要更多的病人接受。其实想想挺吓人的,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不知道这辈子会放一个什么东西进大脑里,这不是假的。所以这个市场还是很广阔的。在我们神经外科存在一个专门的分支叫做功能神经外科,我们有血管神经外科、肿瘤神经外科还有功能神经外科,功能神经外科就是聚焦治疗功能性疾病,比如疼痛、睡眠障碍、帕金森、记忆力下降等等,都可能都是这些技术的应用场景。
主持人:赵总怎么看从科研市场、医疗市场、消费市场的高质量商业化落地?
赵瑞麟:我特别同意前面几位说的,我们既然要做一个公司肯定要对股东负责,对各方面负责,马斯克Neuralink的模式在中国发展是不现实的,一直烧钱,我知道创始人也都走了,关系也不大,公司会继续往前发展。我觉得在中国短期还是要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商业计划,能够最后为投资人带来回报,而且不可能永远烧钱,烧几年钱要有脚踏实地的办法,否则我相信在中国,无论是现在的环境,大家知道现在的融资环境很不好,即便一年前、两年前的资本市场我相信也很难。
这个作业早晚是要交的,现在交或者再过两年交都是要交的,不可能永远画大饼,这不现实,这是我认为在中国做公司和在美国做公司的不一样,美国公司可以在一个点上说有创新,可以在这个点上或者成功或者失败,但是中国公司还是要踏踏实实给投资人一定的信心,比如在有限的时间内、在某一些节点上有现金流。
主持人:问一下景昱的宁总,您可以再介绍一下,包括过往的经验,在外企,包括现在在景昱已经成功商业化了帕金森的脑深部电刺激设备,您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商业化是怎么高效和高质量落地的?
宁益华:在脑科学领域,特别是脑疾病治疗领域有这样一个现状,目前大家都在探索的疾病治疗,很有可能国外都没有相应的技术。中国医疗器械从2005年第一个浪潮高速地发展到现在,大部分都是属于进口替代。已经把市场开拓出来,要分一块蛋糕,都是在做分蛋糕的事情,但是在脑科学领域我们要做得更多的是做蛋糕的事情。
帕金森别人也做了,我们进去分一块蛋糕,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练习我们将来在新的治疗方案上怎么做蛋糕。这个其实大家还没有感觉到,但是我们深刻体会到未来对脑科学从业人员来讲,特别是脑科学领域要商业化的公司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此前真正全球能把新的治疗方案落实到市场的,都是那些大公司,这是我们脑科学公司巨大的挑战。
这是我对未来的预期和经验告诉大家。
4. 新格局下脑科学发展展望
主持人:高质量的商业化是非常有挑战的,是不容易的。我最后想问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未来3到5年,从任意方向或者任意角度,想请各位嘉宾点评一下脑科学在国内的发展前景。先请宋院长您从临床的角度,因为您是一线见到最多脑。
宋冬雷:从临床一线的角度我们对于公众神经健康非常关注,而且我们对于临床和新的产品非常关注,而且需求很大。人有两个需求,一个是活得长,生命要长,第二是活的质量要高。活的长跟肿瘤、血管有关,涉及到死亡,所以要活的长要解决这些问题。但要活的好,比如听得清、看得见、手能动、吃的下、睡的香,记忆力好,这就是活得好,跟功能神经外科相关。
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以后,功能神经外科需求越来越大,这是一片蓝海,而且将来完全是一个可以超越肿瘤甚至超越血管的大市场。其从神经外科角度来讲,我们希望每个人通过我们手术或治疗方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健康、更高质量的生命,所以希望你们好好努力,我们一定加紧使用,只要你们有好的产品,我们一定非常喜欢使用,所以我们要多交流。
主持人:您怎么看未来三到五年,脑科学在国内发展先机?虽然商业化是很困难的。
彭雷:你对未来看得越远,对当下就不那么焦虑了。未来三年,在一些特定功能神经外科应用场景里面,我觉得会有一些明确的医疗产品进到注册临床阶段,我们也有相应计划。不管是资本市场也好,社会对我们关注也好,我们想强调脑科学需要长期主义思维,今天早上包凡总也分享了过去十年和未来十年变化,我们想说的是这个领域是可以真正穿越周期的行业。所谓穿越周期,我们既要看短期三年能做的事情,又要看五年,十年,十五年。所以我觉得除了当下看到的机会,未来想象空间跟天花板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也会持续在这个行业里面探索N个三年取得的答案,而不仅仅是第一个三年的答案,这是我们的思考。
赵瑞麟:我记得有一个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一般来说,大家会高估近期期望值,但会低估中长期、远期的期望值,脑科学比起现在来看规模最大的心血管领域来说,这个行业处于婴儿期,将来成长空间肯定是非常大的,但在未来三年,我相信多数还是处于科研、实验室的突破性发展阶段。
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工程学走到神经科学前面了,突破某一个疾病有一定进展,现在最大疾病是老年痴呆,现在老年痴呆哪怕无法治愈,有一点改善都可以拿注册证,这些恐怕是要一点点积累的,某一天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恐怕还需要时间,所以我认为这三年还是一个过渡、积累的过程,以后爆发式发展肯定是长期的过程,我们还不知道天花板在什么地方。
宁益华:对于很多投资机构的人,我可能会稍微泼一点冷水。做脑科学,应该从更长周期看问题,首先这是一个医疗器械,而且是三类的,一般都要植入,还涉及到电的。所以从医疗器械研发周期和拿证周期来说就是很长的一个时间,按现有规律,没有6到7年基本出不来一个产品,所以我们更应该看脑科学发展未来十年、二十年会怎么样,我觉得刚才宋院长讲的特别好,我们也看到了在未来整个脑功能疾病,会是人类一个最主要要攻克的地方,这其中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个过程也是应该有更多做研究、做临床还有做企业的人一起参与,未来三到五年还是属于积累的过程,会有一些星星火火出现,包括在国外以及中国,但是真正大规模发展还是要靠星火燎原,这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的过程。
主持人:非常感谢各位嘉宾的回答,没有其他问题了,到此结束。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